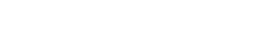美育,也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是教人认识美、感受美、创造美的教育,在当代的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位置。虽然“美育”之名由18世纪德国教育家席勒在其著作《美育书简》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但美育之实却是古已有之的。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都对美育有过深入的思考与实践,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宝贵的经验。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对美育的人格培养作用十分重视。换言之,美育承担着一部分不可或缺的德育功能。厘清中西方审美教育在人格培养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对当今的教育工作有很大裨益。
寓美于善
亚里士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普洛丁说:“善在美的背后,是美的本源。”康德则认为“美是道德上善的象征”。类似的,孔子十分重视乐教,他相信“乐者,通伦理者也”,他理想中的音乐是“尽善尽美”的;荀子更是提出“美善相乐”的观点,强调审美活动对道德的感发作用;《说文解字》中也以“善”释“美”,认为“美与善同意”,可见中西方对美与善的关系认识是趋同的。
先秦时期,乐教是美育中最受关注的形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作用很快被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在书法史中,王羲之“书圣”的地位素来是不可撼动的,对于这一点,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给出了原因:“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换言之,相较于其他书家各自的偏失,唯有王羲之能达到“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境界,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德性,因此他的书法是无与伦比的。
西方的许多艺术实践往往也含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古希腊的雕塑中,诸神祇和英雄都是常见的题材,这些人物往往拥有勇敢、无私、坚毅、智慧等美好的品质,扮演着城邦守护者的角色。比如18世纪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用一种近似于受难殉道的绘画形式,纪念和赞颂了为理想而死的革命者马拉,显得发人深省、动人心魄。
苏东坡曾说:“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所谓的“兼论其人生平”,实际上是把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与人品也当成了审美对象,其评价标准也必然会从“美”延伸至“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外向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要之,艺术属于全人生,而为各个人品第高低之准则所在。”
寓教于乐
好的艺术是美与善的统一,好的美育在提升审美的同时也能感发我们内心的仁与善。那么,这种美与善的互动是否意味着某种说教或者道德压力呢?答案大概是否定的。事实上,东西方的贤哲都非常重视艺术与审美的自发与自由。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所强调的艺术活动中的“游”,正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类似于曾点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理想。庄子的“逍遥游”更是影响了后世许多艺术家。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书法理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宋代“以人论书”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对书家的人品非常看重;另一方面,他眼中的书法又是自由、快乐、放松的游戏。他提出了“学书为乐”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苦闷难熬的炎炎夏日,欧阳修常常“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顾也”,又感慨,“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在他的眼中,书法的魅力几乎是无可取代的。
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曾提出“游戏翰墨”的观念,“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在许多画作的题跋落款中,他都自称是“戏笔”“戏作”。例如他在《洞庭渔隐图》上落款“梅花道人戏笔”,在《渔父图轴》题款“梅花道人戏作”等等。在《吴仲圭四友图卷》中,吴镇甚至将自己的艺术生涯总结为“游戏墨池五十年”。同为元四家的倪瓒也称自己学画是“披图弄翰学儿嬉”,足见文人画“笔墨游戏”的自娱属性。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和理论。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发现了艺术与游戏的潜在关联。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席勒则认为,游戏是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是人摆脱动物状态达到人性的重要标志。毕加索说:“我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马蒂斯也说:“我必须毕生像孩子那样看待世界。”这其实都体现出艺术家对孩童天真烂漫的艺术态度,也即“自由的游戏”的追求与向往。
在谈及艺术“自发”“自由”“自娱”的属性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艺术究竟应该是纯粹而不涉功利的,还是承担着某种外在的目的性?艺术的自娱属性与其道德教化的功用之间有没有冲突?其实,这种困惑的产生,源于我们对主客观的混淆,特别是对“功利心”和“功利性”二者的混淆。“功利心”是一种主观的企图,而“功利性”是一种客观的属性。我们固然不提倡以功利的态度参与艺术实践与审美活动,但站在擘画者的视角,良好的美育会给社会带来正向的受益,这是一种客观规律。也正因此,荀子才会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席勒才会强调,要用美育来完善近代社会中被分解的人格,从而改造社会。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贤哲都构建起了一套寓教于乐的理论体系,从个人兴趣到人格培养,从主观上的自娱到客观上的利他,层层递进,最终完成由个人到社会的价值实现。
化育无声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在其中感觉到越少的教育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净化说”,认为悲剧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疏泄和平衡,从而达到道德净化的作用,这其实就是一种不着痕迹的教化构想。
中国的先贤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孟子曾列举出五种君子的教育方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有如时雨化之者”。北齐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足见熏陶浸淫之作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呢?历代文人士大夫为我们探索出两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其一是营造一种宽广厚重的审美纵深。例如,面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们一方面惊叹于颜真卿苍茫恣肆的用笔、遒劲飞动的字势,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被书写者悲愤的情绪所感染,不可避免地沉浸在安史之乱的惨烈与颜氏一门拼死抵抗的忠义大节之中。正如苏东坡所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这种审美不独囿于书法的形式美,更有书法家的人格之美充盈其中,在不知不觉中给予我们深厚的滋养。
另一种方式则是将生活中常见的形象或情境审美化,赋予他们特殊的意义。例如,渔父本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形象,但古代文人往往将其视为隐士的代名词,《渔父图》这一题材的绘画便由此寄托了文人归隐田园的情思。至于儒家著名的公案“孔颜之乐”“曾点之乐”,乃至陶渊明的田园之乐,都是把生活本身“审美化”的例子。沉浸在这样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心灵怎能不被净化,人格怎能不被陶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作为近代中国美育的首倡者,蔡元培也认为:“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美育之所以承担了一部分不可或缺的德育功能,正因它具备寓美于善、寓教于乐、化育无声的特点,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或强势灌输所不能企及的。总的来说,中西方审美教育中对人格培养的重视是类似的,前者拥有更为丰富、更为细腻的美育实践,后者则建立了更加精密、逻辑性更强的理论体系。中西方在这一命题上如能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一定能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为社会带来更加长远的福祉。
(作者:高峰,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璇,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