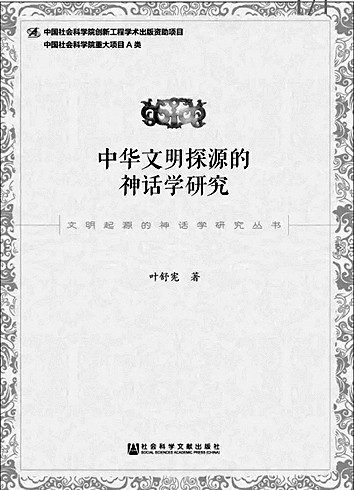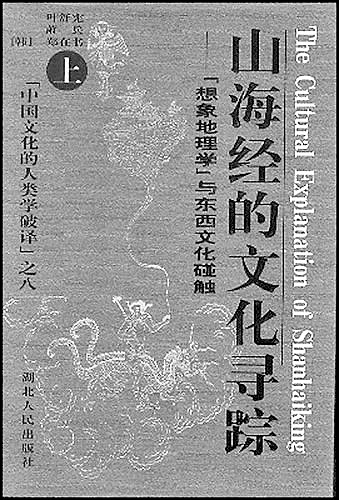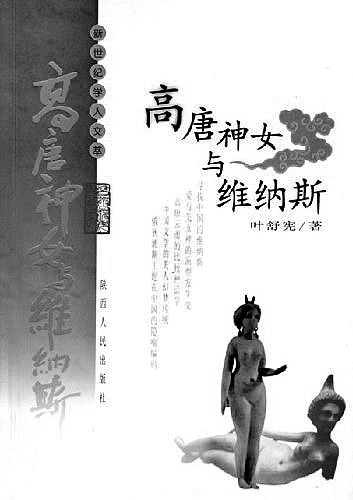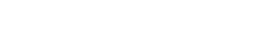【求索】
叶舒宪教授1987年主编、主译论文集《神话——原型批评》,1992年又出版专著《中国神话哲学》,至今数十年间,他已出版了60余部学术著作(含合著),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还翻译、主编了多种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学殖强健。这是长期付出巨大心力、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甘苦,大约只有浸淫于学问中人才得体会一二。
叶舒宪是一位视野宽广、思维敏捷、勤奋笃行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其所长期从事的关于中国神话的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他所创获的学术成果,在当今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评述、概括王国维学术研究特色时说,观堂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百年以来,我国人文学科的代代学人,踵学术前贤而受濡染者多矣,叶舒宪是其中习得的一位。
神话:文化的编码和基因
叶舒宪教授关于中国神话的原型批评,始启于荣格与弗莱的原型批评学说,却并未拘泥于此,亦步亦趋。荣格与弗莱的“原型”说,一般地局限于精神分析的“集体无意识”论与文学溯源的视野范围。前者称,原型作为“种族记忆”,是神秘的“集体无意识”;后者以为,神话作为一切文学的“原型”,是“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云云。叶舒宪以为,这两者都是颇有局限性的学术理念,在对荣格、弗莱原型说有所接受而批判的前提下,可以争取在学理与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叶舒宪说,“我在20多年前(引者按:约指20世纪80年代中叶)翻译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时,基本上延续的是文学性的神话研究路径”“近十年来,希望把神话从文学本位解放(或者称释放——原注)出来,作为文化的编码和基因来看待”。他谈到,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深受艾利亚德的启发,不过他还只在文学范围谈原型,局限性明显”。他意识到,“神话是文、史、哲、艺术、宗教、心理、政治、教育、法律等的共同根源”“人类学的‘文化文本’概念,足以打通以往相互隔绝的学科关系。像文学文本、艺术文本、历史文本等等,统统可以视为文化文本的某种形态,处于同样有待于诠释和解读的召唤状态”(廖明君、叶舒宪访谈《迎接神话学的范式变革》)。这里所言,从关于神话原型的文学理念,到将神话原型批评释放于文化研究这一范畴领域,便是叶舒宪所认知与践行的“人类学转向”。
这就不难理解,譬如关于《山海经》,为什么鲁迅先生称为“古之巫书”(《中国小说史略》),而叶舒宪将其改称为人类学意义的“神话政治地理”了。鲁迅“古之巫书”这一学术结论,虽然写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但实际已经是一个人类学意义的学术判断。叶舒宪将《山海经》看作“神话政治”之作,证明他所接受的人类学神话观,是西方人类学界一贯颇为流行的神话学大概念。这是因为,他将《山海经》这样有关灵玉的巫文化,也归类于“神话”范畴之内,不妨称为“广义神话”说。的确,西方关于神话的文化人类学,一般将原始神话、图腾与巫术等,都划归于这一神话学大概念之下。叶舒宪断言,“全世界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由神话编码的”,这是将弗莱关于“神话”为一切文学的“原型”理念,改造为人类一切文明的“原型”即神话。叶舒宪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所有传世典籍中,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跟《山海经》平起平坐”。《山海经》所载录的众多神山的“神话”中,“有140多处产玉,没有一部可以比之”,而以往学界“把神话文学化”“只研究类似童话故事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是研究中国文化最大的误区”。他要求“把过去文学化的‘中国神话’这个概念,反过来叫‘神话中国’”(《“〈山海经〉虽极难懂却独家保留重要文化信息”》,《经济观察报》)。这一称《山海经》为“神话”的看法,无疑受启于来自西方的“广义神话”说,值得就其原型意义加以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
这里补充一句,与“广义神话”说相应的,是“狭义神话”说,便是把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原始文化形态,统称为“原始‘信文化’”,原始神话仅为其中之一。“原始‘信文化’”这一新倡的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概念,将“三位一体,各尽其能”的原始神话、图腾与巫术三者包罗无遗,三者的共同文化特质,是人类原始宗教文化诞生之前的原始信仰(王振复《原始“信文化”说与人类学转向》)。叶舒宪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有关神话大概念即“广义神话”说的理念与方法,他的神话原型研究的视角,显然与“狭义神话”所倡不一。
神话与历史:共同揭示“历史真实”
所谓“神话历史”说,由美国学者唐纳德·R.凯利首先提出,初见于其《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1999)一书。该书指出:“神话代表着‘希腊人的全部精神原料’,因此是历史本质之所在。”这就无异于说,神话与历史,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1世纪初,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约瑟夫·马里撰写了《神话历史》一书,认为唐纳德·R.凯利在其著作《兰克时代的神话历史》中“将神话历史作为反对兰克学派之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运动而提出来”(见叶舒宪、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神话历史”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是人类学而非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这也便是说,人类学所认同的“神话”,是就整个人类文化而言的,而且兼属于历史学的一个范畴,它蕴含着人类的“全部精神养料”,因而是“历史本质之所在”。
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神话历史”理念,主要用于研究关于原型的中国神话与历史相系这一学术课题。他指出:在原先强烈的“学科本位主义束缚下,神话概念只是在文学学科内得到合法地位和相应的研究”,这就遮蔽了从人类学探究中国文化原型的可能。从人类学神话原型说这一角度看,神话的文化性与历史的文化性相契,因此,“‘历史’和‘神话’相互分割对立的僵化局面”必须被打破。的确,“神话的内容和神话讲述活动本身都显露出充分的历史性,历史叙事中也显露出充分的神话性”(同上)。
这一学术判断,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与评说呢?譬如,汉代大史笔司马迁撰写的皇皇巨著《史记》,是从撰写神话传说中的五帝及其时代开篇的,关于黄帝、颛顼、帝喾与尧舜等的“生平事迹”,都作为“历史”来写。太史公曾批评那种“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的缺失,称其自己曾经“西至空桐(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经过了广泛的“田野考察”,等于认为其所写的《五帝本纪》,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并非出于虚构,因而与诸子百家所写的“黄帝”之类不一。司马迁自然不懂得什么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神话学,但他将关于五帝的神话传说,当作历史真实来写。他真诚地相信,五帝是真实存在过的,否则,他不可能排出一个黄帝的族谱来。
问题是,《五帝本纪》所记载的,真的是关于黄帝等远古圣王的一部纯粹的“信史”吗?假如神话等于历史,就可能泯灭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远古的“圣王”事迹,往往有着神话传说的成分。历史是关于曾经存在过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等有关具体时空的记述,绝不允许无中生有、凭空虚构。神话则不然,无论是文学抑或人类学意义的神话,恰恰都是以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幻想、夸张与虚构为其生命的。可是,人们也许忘记了,虚构的神话,先以口头继而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存在,本来便是人类远古生活的事件之一,理所当然是人类历史的有机构成。历史与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两大极端,都以人类的原始生活为场域,在揭示“历史真实”这一点上携起手来,形成“对话”。因而,在笔者看来,当我们以人类学的“神话历史”观进行研究时,应当承认:神话与历史的人类学关系是既合二而一又一分为二的。
有西方学者把“神话历史”定义为“一种混合着虚构的寓言和传说的历史”,叶舒宪认为这是可取的,指出“神话历史”说“预示着比较神话学将取得以往从未有过的学术跨度与大拓展的知识条件”(《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以为“神话历史”说最有创意的一个方面是提出文明之前的历史是由原始神话参与创造的,这一看法,学理上可以成立而且很有见地。某种意义上,原始神话等同于人类的上古历史,神话与历史作为叙事,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合二而一”的一面。
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还有另一面。神话所记述的,远远不是人类原始生活的全部,神话一定遗落了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历史所可能覆盖的面,要远远超过神话,神话所揭示真实的叙述方式,也殊异于历史。这同样可以证明,神话既等同于历史又有异于历史,两者的关系,确实是合二而一又二律背反的。
就原型探讨而言,叶舒宪认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口头神话、书面神话,都经过了“N级编码”,尽管那种真实本然是一种“在”,其神话言说却往往是扑朔迷离的,难以彻底了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在”以及其何以“在”。因此,我们必须如王国维那样,“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认真、细致、科学地互相参证。
就神话原型来说,值得加以厘清的有:是真正原型意义的原始神话,还是次原型或次次等原型意义的神话;是关于神话的最原始的虚构,还是无数次虚构之后的虚构,等等。
叶舒宪所从事的这一学术领域,由于他与许多学者的共同探索,确实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原型意义的“神话历史”研究提供了学术创新的可能。然而,这一学术领域所涉及的“人类学难题”颇多,难以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叶舒宪说:“未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其一,如何采用神话历史新视野去全面解读中国的‘二十五史’?其二,神话历史的观念如何在‘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拓展出更加完善的分析范式与概念工具?其三,神话历史的观念如何促进从‘中国历史’到‘神话中国’的研究范式转换?”(《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凡此关乎神话历史的真实与原型问题的发问,确有开拓学术思路的一面。
中国玉:玉成中国
叶舒宪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其一,从文学转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序幕”,却并非可有可无。他所说的“文学人类学”,实际是文化人类学,他的神话学观念,归根结底属于人类学;其二,以西方人类学关于神话原型说的译介为契机,先是利用文献进行了诸如《山海经》等的神话原型批评,揭示譬如《山海经》的有关记述与甲骨文“四方风名”的对应等,继而转向“中国玉”这一东方独异之“灵物”的神话原型批评,注重与西方神话原型说的比较,坚信可以从远古神话意义的这一神异之“灵物”,追寻中国文化的根因根性,即其历史与人文原型。叶舒宪所主要从事的,是关于文化“物态”而非文化“形态”的人类学研究。
叶舒宪抓住了“中国玉”这一特殊文化的“中国问题”,他的学术期待首先在他与著名学者萧兵等亦师亦友、合作良久而取得的不少成果中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这些成果变革了从谢六逸、闻一多、鲁迅、茅盾到袁珂等学者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研读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和《〈旧约〉中的民俗》等西方人类学经典,是叶舒宪由文学研究转向人类学关于神话原型批评的一大学术契机。他说,“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人类学”。
这一个“迷”字,生动地凸显了叶舒宪一贯的学术态度。无论做任何学术,一位学者的精神境界假如能够进入虔诚的迷恋状态并且锲而不舍,倘若做到孔夫子门生子夏所言那般“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的境地,那么他离学术上的大获其成,可能也就不远了。叶舒宪是一个愿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的学术经历也再次雄辩地证明,王国维所说的“学无中西”(《国学丛刊序》)一语,作为研究理念与方法,是具有一定真理性的。在中国学界,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中”,一直是有争论的。诚然,这一“学无中西”、以“西”释“中”之“学”,应是批判地看待西学而努力结合本土进行研究,而后才可能有所创获。
叶舒宪关于“中国玉”的文化原型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持续近五年、完成了15次探玉考察。这一“准田野”(有别于考古人类学的田野发掘)的考察活动,覆盖我国中西部七省区的260个县域,对史前玉器和玉料产地进行数据和标本采集,推出了三套丛书和电视纪录片,提出了“4.0版”西玉东输历史。
从西方人类学研究史看,田野调查这一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大约始于1846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北美易洛魁部落的“田野作业”。此后,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将其提升为西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方法论而受人尊重。人类学研究重视“田野调查”,但人类学研究又不仅仅是“田野”。无论“田野”还是“书案”,关键在于真正践行“科学”二字。我国的历史学领域,曾经有“疑古”与“信古”两大潮流,应当说,二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科学因素在,未可一概否定。然而在根本意义上,值得大力提倡的,归根结底是科学的“释古”。当今诸多学者,包括叶舒宪教授,都为此而努力实践着。
做学问,殊为难得的是达到历史与逻辑、实证与理念的真正统一。假如没有逻辑,世界便杂乱无序,根本不会有学术理论与思想的系统建构。一旦不注重实证,则所谓的理念与理论“建构”,便会因缺乏学术上的真正洞见而沦为无根的“研究”。对于神话原型批评而言,也总是历史、实证优先的,这是一个铁律。在某些学术偏于空疏而无当的今天,叶舒宪等重视并践行田野考察,谨严治学,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叶舒宪教授有高远的学术抱负,对一些现存的学术之见,往往投以质疑的目光。是的,学者首要的学术能力,首先在于自觉地意识到,学术上凡是已经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问题意识”催动其进入研究历程,而后才有解析、实证和解决问题的可能。这证明,所谓学问,“问”比“学”更为“本体”,对于学界不时提出的新命题,唯有在不断进行实证与理念相统一的研究之后,才可能判断其真伪、是非。叶舒宪提出、论证过诸多学术命题,如“大传统、小传统”与“四重证据”说等,这些是属于治学方法论方面的;又如,他认为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中国有一个“玄玉时代”,提出“玉成中国”与“原型编码”说等等,凡此都是叶舒宪学术思维颇为活跃的明证。
这里仅就“大传统、小传统”说略言几句。他说:“什么是大、小传统呢?我们针对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反其意而用之:将汉字编码的书写文化传统,即将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这一套文字叙事,称为‘小传统’;而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即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和书写传统并行的口传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比如崇拜玉、巨石、金属(青铜、黄金等——原注)的文化等。”(《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这种“反其意而用之”的学术思维,是“接着讲”兼“反着讲”。他将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把文字书写传统视为大传统,把无文字的乡民社会看作小传统”的看法,加以改造而自裁新见,显示出他的学术眼光。
叶舒宪将人类无文字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强调了这一传统的“原生”意义。这里的“大”,甲骨文意义为“本始”“原始”,它与人类有文字之后“小传统”的“次生”性,有本次之别。笔者以为,后起的“小传统”文化,对“大传统”必然总是有所遗忘、有所选择、有所“遮蔽”,然而“小传统”作为“子”文化,除了“遮蔽”,同时还有“开显”的一面,不可能与作为“母”文化的“大传统”毫无关系。某种意义上,“小传统”是“大传统”具有真理性意义的文字记忆和表述,必然赓续文化“大传统”的诸多文化血脉。关于这一点,叶舒宪教授表述为“小传统之于大传统,除了有继承和拓展的关系,同时也兼有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他的着重点在于强调“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取代”和“遮蔽”,目的在于凸显神话原型批评、原型研究的不可替代性,是可以理解的。而“小传统”中,同样蕴含着文化原型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关键在于要有一个科学的立场和操作。
一个有学术理想、追求实证与理念相统一的学者,在尊重实证的前提下,首先得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始终以实证兼逻辑的方式,加以证是或证非,这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叶舒宪教授提出的一些学术命题,是在有所实证的前提下提出的,而这里值得进一步思考、讨论与加以实证的课题甚多。实证与理念相统一的追摄,是一个无尽的认知、实践过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实证、理念以及两者达成真正的统一,是把握学术真理的必由之路。
叶舒宪专注于灵玉这一史前之“物”的神话原型批评,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未阻塞其他与此不一的研究视角、方法和途径。笔者相信,为了实现如原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所言“做第一等学问”的崇高目标,多种学术见解之间的探讨甚而争辩,是必要且理所当然的。
(作者:王振复,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