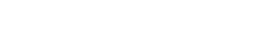王蒙:我怎么能冷漠,我怎么能躺平
2021年12月27日 16:29:08 作者: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2月22日 18 版) 审核:
十来岁时,王蒙首次看了1938年敌伪时期上海拍就的电影《雷雨》。印象最深的是侍萍与周朴园重逢,侍萍提到三十年前的事,说:“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
少年王蒙听到这妇人回忆往事,也感到心头沉重,为一个在没有火柴的年代生活过的人黯然神伤。
二十四岁那年,他读到毛主席《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肃然起敬,“恭敬而且惭愧,自卑而且伤感,反省而且沉重”。
那个时候,他尚不可能想象:一个即将满八十七岁的写作人,从六十三年前的回忆落笔时,应该出现什么状态,什么样的血压、血糖、心率、荷尔蒙、泪腺、心电图与脑电图……
他毕竟还是写了。在《猴儿与少年》里,他写了若干只猴子。其中一只名叫“大学士三少爷”。它们是王蒙小说里的至爱。
评论家谢有顺说,王蒙依旧在他的文字世界里热火朝天地劳动着,他热爱劳动,念念不忘土地、人事、岁月对于他的滋养。“常胜者常挫,常健者常恙”。的确,《猴儿与少年》是《青春万岁》的回声。
2021年12月17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北京召开期间,本报记者专访第八次参加作代会的王蒙。
1
中华读书报:写革命人的故事,离不开革命。政治在作品中出现,言简意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概括中国社会发展之变化,高度浓缩,高度凝炼。您如何处理作品中的政治?
王蒙:二十与二十一世纪,政治是中国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谁的生活脱离得了政治呢? 对政治的体悟、感受、态度,当然各有特色。友人诗里有一句:“为人不革命,此生不足论”,此警世警文坛之语也。
中华读书报:在《猴儿与少年》里,英语、德语、日语、俄语一齐上阵,老子、曹雪芹、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康德先后亮相,化学、数学、哲学各有所用,京剧、相声、电影点缀其间……这几乎是百科全书了,十八般武器全操,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大到对生命哲学的体悟,小到对一个词语的解释,但仍然诗意充沛、酣畅淋漓,您现在的写作是否已如入无人之境?
王蒙:我说过,近七年,我恢复了以写小说为主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写起小说来,每个细胞都在跳跃,每根神经都在抖擞——嘚瑟。
我还说过,耄耋写小说,回忆如潮涌,思绪如风起,感奋如雷电,言语如铙钹轰鸣。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句子,都牵连着光阴,亲历、亲睹、亲为,联系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联系着四面八方、千头万绪、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连结着多少爱恋挂牵,明明白白,回味无穷。你不撒开写,难道要缩手缩脚地抠哧吗? 一天等于二十年,一辈子等于多少天呢? 纪念着一个又一个一百年,怀想着几千年几万里,用八十七年的生命教训与几万里的所见所闻写,与用十几岁的少年初恋之情写,能是一个样儿的吗? 我还说过,我还是文学生产上的一线劳动力啊!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书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哨子,都吹起来吧!”还是《青春万岁》饱满热烈的情绪! 还是诗意的、激情的王蒙! 为什么八十七岁的您还能保持十九岁的少年心和少年性? 您是怎么做到依然葆有十几万“立方”(书中语)的激情?
王蒙: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难、严肃的选择、奋勇的冲锋、凯歌的胜利,欢呼与曲折,艰难与探索,翻过来与掉过去,百年——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未有的历史变局,千年未有的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我活着经历了、参与了这一切,我能冷漠吗? 我能躺平吗? 我能麻木不仁吗? 我能不动心、不动情、不动声色,一式36.5℃吗?
2
中华读书报:“炳炎儿时不就是一只小猴儿吗,他的感悟与小猴又有什么不同呢?”——小说讲述九十高龄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的人生往事,“王蒙”的出现,总让我在阅读中有一种代入感,觉得施炳炎确有其人,“三少爷”也确有其猴。为什么想到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 怎么想到给猴子起这么一个名——“大学士三少爷”?
王蒙:这里有一个自我认同与自我分离的问题。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每个人又都是自己的发现者、观察者、评点者、挑剔者与顿足批评者或怜悯宽恕者。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小孩,他正是“我”啊! 惊奇、畏惧、被吸引,同时百思不得其解。《红楼梦》里有贾宝玉与甄宝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这才是小说啊。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有沐猴而冠的说法,猴儿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有弼马温气质,有天真的官迷气质,又有少爷的任性与骄矜,又有学士的多才多艺,能干机灵啊。
中华读书报:猴子与其他宠物的不同,是作品中施炳炎的思考,相信更是您的观察和结论;作品中用陶制原始乐器埙的闭口吹奏声音比拟猴儿鸣叫,对它的各种动作观察细致入微。您对猴子是不是也有特殊的感情?
王蒙:我小时候没少看耍猴儿戏。有了孩子,动辄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猴山。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到处是猴子的大街上,由于对猴儿们指指点点,受过猴子的奚落和抗议,作鬼脸、出怪响。我也通过各种渠道,线上线下找猴子的生物学与社会学资料。为了写这篇小说我还特别请教过善画动物的美术天才韩美林兄,得到他的帮助,写起猴子来,其乐无穷。
中华读书报:“照镜子”一节写得奇妙。施炳炎从乡民们对三少爷照镜子的言语中,想起《红娘》中红娘侍候莺莺照镜子,也是自恋自怜。您观察过猴子照镜子的真实反应?
王蒙:照镜子是人生的一大奇迹。镜子与镜子相对而照,出现了无数镜子的映象,叫作长廊效应。贾宝玉曾经在镜子中睡觉,梦见了甄宝玉,这个构思极其有趣,哲学的趣、人生的趣、文学小说学的趣与社会学的趣。甄宝玉没有写立体、写生动、写真实,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遗憾,但是,这个构思仍然是超级观察与想象的绝门儿。许多读者与评论家注意猴儿照镜子的情节,使我至为满意。
3
中华读书报:“病乎”一章耐人寻味。您在小说里凝聚了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当下、对历史的种种思考。
王蒙:我有一些这方面的实际遭遇与观察体验,急剧的发展变化,带来个中角色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医学话题。一切的发展,都令人欢呼歌唱,一切的进步,也都有自己的代价与新的挑战与麻烦,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啊。
中华读书报:大核桃树峪的民歌,是确有其歌? 第六章“高峰大树”,开篇有说诗歌不是诗歌,像词不是词,又压韵上口的一段,是性之所至随手写下的吗? 总之这部小说充满音乐的节奏感。
王蒙:除文学外,对音乐我也是最为迷恋的。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里头加诗歌体、词赋体、绕口令体、乃至其他文体的笔墨,使小说变得充分立体化,其范例就是《红楼梦》。抡起来了,您就飕飕飕地往圆里抡吧。
中华读书报:刘长瑜说吴素秋是“女才子”,小说中王蒙回应施炳炎的疑问时,提到部里有文件“避免男孩子的女性化伪娘化”;作品中赞赏红娘,讥讽张君瑞是“爱情的乞儿”,是否也是对当下某些现象的一种反讽?
王蒙:封建主义使男生弱弱的,也是确有其事。但张君瑞的情况不是女性化,而是书生懦弱化。查字典或找《荀子》看看,儒字甚至可以与懦字相通。呜呼。
中华读书报:施炳炎转述给“王蒙”的侯东平“有活儿论”,很经典。这本书也是充满哲思的作品,既有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也有“炸糕八里地,白薯一溜屁”等民间谚语,整部小说如您所说“生活的热气蒸蒸腾腾”。孔孟老庄易经您也都有研读。您从中国传统文学汲取了很多智慧。
王蒙:如果你接地气,如果你接触过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如果你听过地方戏,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中国特色了。艺术从业人员喜欢用“活儿”一词,我听一位歌唱家说到国外的一位乐队资深指挥,说“他社会地位很高,就是活儿糙”。我明白了。你喜爱了、进入了、从事了文学艺术,可关键是您得出活儿。让活儿说话,靠活儿立身,以活儿贡献,为活儿忙活。
中华读书报:小说借主人公说:这是中国,您要到山里来,到村里来,否则仍然是没见闻过中华醇香。这是主人公对土地的眷恋,是对人生过往的总结和怀念,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深入生活的呼唤,您觉得是我过度诠释吗?
王蒙:您诠释得太棒啦! 在中国,我们说生活,常常离不开山沟,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好多朋友大谈毛主席喜欢讲“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今年更讲山沟里脱贫的伟大成就,当然还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山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
4
中华读书报:您参加几次作代会了? 有怎样的体会?
王蒙:从作协三大开始,参加作代会应该是第八次了,但作协九大没有参加,上次开会时我正在圣彼得堡参加文化论坛,忙着见各国的文化人与俄罗斯的领导人了。会上与会下,国外与国内,我都没有忘记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生活经验是基础,文学想象是翅膀,多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学问是资源。然后,要的是热情与勇气。
中华读书报:“后世的小友,不懂得我们那一代人的快乐和天真天趣与哭笑不得。”您写的时候,除了纪念、怀念,是不是也有些怅然,有交流的欲望?
王蒙:与其说什么怅然,不如说是经历过实实在在的艰难,还有克服困难,化险为夷,遇难呈祥,终结善果。薪尽火传,一代与又一代不会断裂,不要用断裂吓唬人。但一代一代不会重复,各有各的青春万岁,各有各的万里长征。谁都会成长成熟老练坚定;谁都不是吃素的。
中华读书报:施炳炎是乐观的,但他也不出声地大哭过一场,哭得昏天黑地、荡气回肠、天旋地转、痛快淋漓、落地扎根、刻骨铭心。为什么哭,是因为侯东平对他的宽慰吗?
王蒙:施炳炎曾无师自通地跳到圈外,观察他本人与大千世界,有“七个我”,经历了风云激荡、奔突冲撞的世纪,经历了碰壁与风险、坎坷与雷地,有些人甚至曾经认为他是个不无晦气的可怜虫,但是小小农村少年居然对我们的主人公作出政治思想的正面结论,侯东平他们是不在乎这些的,他们是很实际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最后您说“鼓捣新的小说创作”,是否又有新的计划?
王蒙:再酝酿一下吧,说得急了容易被动,而且涉嫌吹嘘——网上叫“newbelity”。